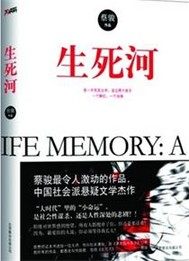漫畫–AQUARION COMPLETE–AQUARION COMPLETE
1995年6月19日,乙亥年壬午月辛巳日,陰曆五月二十二,卯時,兇,“日時相沖,事事失宜”。
我死於戌時。
年年瀟與立秋,我城邑去給萱掃墓,每次都會加油添醋對滅亡的知情。設或身後再有人記得你,那就不濟事實事求是死去,至少你還活在該署人身上。即使如此躺在一座無主孤墳中,起碼你還活在後的DNA裡。饒你連半點血脈都沒久留,低檔還有你的名與相片,留在出生證、假證、戶口本、借書卡、泅水卡、日記簿、畢業考卷……我多怕被大衆記得啊!我叫申明,曾是先秦國學高三(2)班的武裝部長任。
我剛幹掉了一期人,然後又被另一個人殺死。
在拋開瓦房暗的魔女區,有把刀刺入我的反面。
戴着綴有紅布的柔姿紗,我信從和好總睜觀賽睛,傳聞中的死不瞑目,但我沒收看結果我的兇手的臉。
能否歇人工呼吸?權術有消退脈息?頸冠狀動脈還搏動嗎?血一再凍結了嗎?氧氣一籌莫展提供前腦?煞尾發生腦亡?分毫無政府得好消亡。
周朝侯爵家族史書實錄 小說
發奔本身的意識,就是死嗎?
人人都說死的時候會很不快,任由被砍死吊死掐死悶死毒死淹死撞死摔死居然病死……然後是限度的形影相弔。
高校時代,我從母校熊貓館看過一本常見書,對此死滅過程的描畫良善記憶難解——
刷白直挺挺:通俗生於與世長辭後15到120秒。
鹹魚老祖宗她被迫成為頂流
屍斑:殍較低位的血液沒頂。
屍冷:死亡從此體溫的跌。常溫平平常常會穩步下沉,以至於與環境溫度不同。
屍僵:遺體的四肢變得強直,爲難挪動或搖搖擺擺。
腐爛:屍體組合爲純粹表面物質的經過,陪伴着醒目難聞的脾胃。
記憶力無可非議吧。
冷不防,有道光穿透暗水澆地底。我盼一條驚訝的廊子,方圓是瓊的骨材,像魔女區的純碎,又像古舊的春宮。場記下有個小女娃,試穿打補丁的柔弱行裝,流察淚與鼻涕,趴在氣絕身亡的母親身上淚流滿面,邊緣的男人漠不關心地抽着煙——當下鳴脆生的討價聲,他也化作了一具異物,後腦的洞眼冒着煙火,鮮血逐漸流了一地,沒過小女娃的腳底板。有其中年妻牽着異性,開進一條恬靜的大街,名牌上恍寫着“睡眠路”。這是棟陳腐的屋宇,女性住在地窖的窗扇背後,每個晴朗天昂首看着液態水涌動的大街,人們鋥亮或印跡的雨鞋,不常還有夫人裙襬裡的黑。異性雙眸忽忽不樂,未曾一顰一笑,臉蒼白得像鬼魂,僅僅兩頰品紅,怫鬱時更爲恐怖。有天更闌,他站在窖的窗邊,街迎面的大拙荊,嗚咽哀婉的慘叫聲,有個雌性步出來,坐到污水口的階梯上啜泣……
我也想哭。
但我唯獨一具殍,決不會啜泣,只會流膿。
速我將改爲骨灰,躺在紅木或硼鋼的小盒子槍中,酣夢於三尺以下的黃土奧。還是,橫在魔女區烏七八糟陰涼的街上,低度陳腐成一團骯髒的素,連耗子與壁蝨都一相情願來吃,最後被菌物蠶食鯨吞壓根兒,直至成爲一具身強力壯的龍骨。
借使有人頭……我想我熾烈離開軀幹,親口觀殪的融洽,也能視殘殺我的兇手,還能農田水利會爲人和報仇——變成厲鬼,利害的怨念,很久烙跡在魔女區,以至清代普高四旁數公里內。
死後的天底下,簡便易行是冰消瓦解年光看的,我想此怨念會是持久的吧。
而人存,就可以能始終,惟死了。
人從一降生開班,不雖以便候去世嗎?只不過,我期待得太短促了少數。
或者,你們中會有一下智囊,在明晚的某個清晨或晚上,探悉以鄰爲壑我的鬼胎謎底,還要抓住滅口我的兇手。
誰殺了我?
借使還有下輩子?倘或還有來生?如其還能重來一遍?借使還能防止通盤荒唐和過失?好吧,誨領導人員嚴加,雖然我剛殺了你,但苟在另一個中外撞見你,我甚至想跟你說一聲“對不起”!
訪佛睡了良久的一覺,人身捲土重來了感,徒盡人變得很輕,殆陣子磁能吹走,心腸莫名歡騰——這是復活的有時?
情不自禁地站起來,偏離魔女區,前面的路卻這就是說陌生,雙重從來不垃圾堆的瓦舍,倒更像舊書頭像裡的鏡頭。沒譜兒失措地走了天長地久,腳下是一條黑暗的小徑,二者是清悽寂冷的原始林,耐火黏土裡依稀赤白骨,再有夏夜裡的粼粼鬼火。腳下響着貓頭鷹的哀叫,常有長着人臉的鳥雀飛越,就連身段都是才女的形式,可否哄傳中的姑獲鳥?
有條河封阻我的支路,屋面竟恐怖的紅色,空虛桔味的涼風從潯襲來,捲起的怒濤黑糊糊藏着人影兒與髮絲,怕是剛溺死過好幾船人。沿着延河水走了幾步,秋毫沒感覺到驚心掉膽,才挖掘一座年青的公路橋。青的橋欄杆下頭,坐着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子,佝僂着軀幹不知好多歲了,讓我回顧兩天前才辭世的外婆。她端着一下破泥飯碗,盛滿熱火朝天的湯水。她擡頭看着我的臉,惡濁架不住的眼光裡,現某種異常的驚呆,又有些可嘆地撼動頭,生出悲哀乾枯的聲音:“何故是你?”
老嫗把碗塞到我前,我恨惡地看着那層湯地上的濃重:“這是哪所在?”
“喝了這碗湯,過了這座橋,你就能返家了。”
因此,我信以爲真地放下碗,逼協調喝了下去。味兒還不壞,就像老孃給我煮過的豆腐羹。
老太婆讓到一壁,敦促道:“快點過橋吧,否則來得及了。”
“爲時已晚轉世嗎?”
這是我在北漢高中翻閱時的口頭禪。
“是啊,童稚。”
雲上會館
話說中,我已渡過這座現代的石橋,俯首稱臣看着身下的江湖,全方位夫人長髮般嬲的牧草。剛登河沿極冷如鐵的莊稼地,就狂升一陣無語的反胃,鬼使神差地跪倒吐起。
焚世刀皇
真憐惜,我把那碗湯合賠還來了。
當我還從來不轉回神來,後部的淮已忽然高潮,一晃將我淹沒到了水底。
在長滿酥油草俱全白骨的暗中坑底,同怪僻冷酷的光從某處射來,燭了一番人的臉。
那是屍首的臉,也是二十五歲的發明的臉。
而我快要化作旁人。
當年我不親信古籍裡說的——人身後都要長河九泉,走上陰曹路,在抵達九泉之前,再有一條壁壘的忘川水。透過河上的如何橋,走過這條忘川水,就慘去改編轉世了。奈何橋邊坐着一期老太婆,她的諱叫孟婆,倘使不喝下她碗裡的湯,就過不足如何橋,更渡不迭忘川水,但若喝下這碗孟婆湯,你就會健忘過去的方方面面忘卻。
忘川,孟婆,下輩子。真個會忘一齊嗎?
“倘諾再有明朝?你想怎麼着美容你的臉?使付諸東流前?要何許說再見?”